
张仲明,1935年8月出生,上海人。1959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毕业后前往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科工作,曾为积水潭医院烧伤科“八大金刚”之第三金刚。196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到意大利米兰、罗马进修学习。1986年,自创的“深二度烧伤削痂技术”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983年-1992年担任北京市卫生局医政处处长,1992年,任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1996年退休。退休后任中华医院管理学会副秘书长。
采访组:请介绍一下您的成长经历,为什么会选择学医?
张仲明:1935年8月,我出生在上海松江区一个中医世家,从我曾曾祖父开始一直到我的父亲,四代都是中医。我父亲在松江区一带行医50多年,他毕生严肃认真、好学求新,为了实现中西合璧、中药西化的愿望,研制出了很多新型的丸散膏丹,在当时缺医少药的农村,为当地百姓解除病痛和挽救生命做出了很多贡献,也为传承我国中医药发展做了很多努力。在他的言传身教与潜移默化下,我从小就觉得医生是一个治病救人的伟大职业,中医中药是祖国最珍贵宝库,我一定要做一名像父亲一样的好医生。所以我1954年中学毕业后,就考上了北京医学院。
采访组:请您回忆一下从医经历?有没有印象深刻的病例?
张仲明:1959年,我大学毕业,党支部书记找我谈话,问我是不是愿意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我说“服从组织分配!”后来宣布分配方案时,我被分配到了北京积水潭医院,半年前我曾在这家医院“勤工俭学”,而我即将进入这家建成不久,是以骨科、手外科与烧伤科闻名的大医院工作,可以说是非常幸运了。
最初我被分配到了矫形外科,但是我想去“轰轰烈烈”的科室,比如烧伤科。当时正值新中国成立初期,全民大炼钢铁,经常有大面积烧伤病人抢救,我把自己的想法向院领导汇报,得到了院领导的支持,把我调入了烧伤科。
到烧伤科的第一天,看到病房里的病人都是“面目全非”,有的病人全身都烧焦了,有着难闻的糊焦味;有的病人面部烧伤,肿得像个“大头翁”;有的病人是二度烫伤,身上冒着黄水,真是让人害怕。但是我告诉自己,他们原本过着美好的生活,却不幸被烧伤、烫伤,我应该尽己所能把他们从痛苦中挽救出来,慢慢的我就习惯了。
在我接诊的病人中,有一名是面部被化学品灼伤的女大学生,看见她受伤前的照片,是那么的青春、靓丽,我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滋味。每次看到她,都让我感觉身上的责任重大,于是我更加坚定了信心,一定要好好工作,把病人都治好。
工作两年后,医院领导安排我到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陕西、山西、新疆、湖南、湖北、海南、广西参与重症病人的会诊抢救。因为工作表现突出,我作为重点培养对象,参加了《矛盾论》和《实践论》的理论学习,让我明白了医生要会抓住主要矛盾。当时,烧伤科的病人中有很多无法救治,问题根源是持续性感染,所以我们就要抓住控制感染这个主要矛盾。
1958年,上海瑞金医院救治烧伤面积达到89%的炼钢工人邱财康的成功案例,打破了国际权威专家认为烧烫伤超过体表面积80%就无法救治的论断,这让我们倍感振奋,大家努力学习,不断实践,总结经验。1961年,科室连续成功抢救5名烧伤面积大于80%的工人,其中一名工人被石灰烧伤,面积达到96%。1965年,抢救烧伤面积80%以上重度烧伤病人已有40余例,创下了多项世界纪录。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邓拓了解情况后撰写文章刊登在《前线》杂志上。

1965年11月28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的“为革命 会革命”
1965年7月,人民日报记者郭小川和王日东到北京积水潭医院采访创伤骨科烧伤专业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经验,他们在医院蹲点采访了多名医护人员抢救危重烧伤病人的故事,撰写了《为革命,会革命》的长篇通讯,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还把我们烧伤抢救组5位平均年龄27岁的年轻医生讨论病情的照片登载在报纸的右上角。记者王日东撰写了《在斗争中学习运用唯物辩证法》,这篇报道极大鼓舞了我们在抢救与治疗大面积烧伤病人的勇气和信心。
1965年,新疆乌鲁木齐建设兵团被服厂失火,烧伤百余人,医院党委决定派我前往新疆进行抢救支援。因为深度烧伤需要进行植皮手术,卫生部同时指派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孔繁怙教授一同前往支援。

左一为张仲明医生正在查房
病人大多是17-20岁的青年,双手都是深二度和三度烧伤,既往的保守治疗病程长、病人痛苦,而且最后双手易发生严重畸形和功能丧失。为此,我和孔繁怙教授商量,是否打破常规进行早期切痂植皮,以保障病人双手达到最好的外观与功能。孔教授有些顾虑,因为手部整形植皮手术要在完全无菌的情况下操作,而这些病人的双手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感染,一旦植皮手术发生感染,所植之皮均会全部坏死,风险很大。积水潭医院烧伤科以前有过这种手术的成功经验,在我对第一例病人进行手术示范,并讲清如何预防感染的方法以及植皮的技巧后,孔教授同意了我的做法。我们抱着对这批兵团战士今后能重返工作岗位的希望和信心,毅然决然地采用了这种“冒险”的治疗方法。经过几个日日夜夜,开展了几十台手术,为近50名战士完成了70多只烧伤手的植皮手术,植皮全部成功。这可以说是一次空前的创举,孔教授也很感慨地说:“这是一次意想不到的奇迹”。
采访组:您如何看待科研工作和临床诊疗之间的关系?
张仲明:我个人认为,科研和临床是有密切关系的,是相辅相成的。我在积水潭医院烧伤科获得的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深二度烧伤削痂疗法”就是科研与临床密切结合的产物。
经过多年的工作,我在治疗烧伤实践中研究出了一种“深二度烧伤的削痂技术”。烧伤医生都知道,深二度烧伤不好治疗,因为深二度烧伤采取的保守疗法病程长、感染机率高,治愈后瘢痕增生也特别严重。在一次取皮植皮过程中我突然想到,如果用Humb’y取皮刀把深二度烧伤的痂皮像取皮一样削掉,烧伤创面立即变成了一种新鲜创伤创面,是不是就能够替代痂皮自然脱落的过程了?后来我用这个方法进行了多次试验,效果都非常好。随后我又进一步研究了鉴别坏死组织与正常组织界线、削痂后创伤创面如何处理等后续问题,正式向组织提出了深二度烧伤削痂技术的设想,经科里讨论研究和细致调查后,一致同意可以在临床上应用。这个方法简单方便,缩短了疗程,防止感染发生,比切痂疗法减少正常组织的损伤,同时减少了瘢痕增生的概率。后来,全国各地的同行在深二度烧伤的治疗中也采用了削痂疗法。
1980年,烧伤科突然接收了数例大面积磷烧伤的病人,他们收进病房时创面呈现的都是深二度烧伤。磷烧伤与热烧伤不同,热烧伤是一瞬间的热力对皮肤的损伤,而磷烧伤是持续对皮肤的损伤。两者的治疗方法也是完全不同,如果按照以往的治疗方法,磷烧伤持续损伤的特点,深二度创面必然向三度创面发展,将会严重地加重病情。于是,我提出用深二度削痂技术,及时削去磷损伤的坏死皮肤,阻断磷进一步向深层皮肤的侵袭,这个提议得到了上级领导和同事们的赞同。我们还打破了休克期过后手术的常规,连夜进行深二度削痂抢救手术,最后收到了满意的效果,挽救了这几名严重磷烧伤病人的生命。同时也再次验证了这种削痂技术的可行性和有效性。1986年,深二度烧伤削痂技术与上海三度烧伤切痂疗法并列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深二度烧伤削痂疗法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颁发的奖章
采访组:您去延安、西藏工作的事情能和我们谈谈吗?
张仲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医务人员响应毛主席“六二六”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纷纷要求上山下乡到农村、到偏远山区,为缺医少药的农牧民群众服务,服务的形式主要是派医疗队进行巡回医疗。
1965年,我响应号召到北京郊区延庆县进行巡回医疗,发现当地的妇女儿童不仅生活艰苦,还常年生病,妇女生产后总是病痛不断,孩子出生后不是肺炎就是腹泻。我在巡回医疗过程中找到了根源,发现她们主要是营养不良,特别是缺钙引起了很多疾病,不少人在补充钙和维生素D后,身体逐渐好转。
1974年,我参加了北京第四批赴延安医疗队。为了培养当地医生,提高医疗和预防水平,我们手把手教赤脚医生看病、采药、手术。那段时间,我去过宝塔山,喝过延河水,和老区人民同吃同睡同劳动,劈柴挑水、生火取暖、修井改河,样样都干。这一年的时间里,我们为当地老百姓送医送药,解除病痛,但同时也受到了他们的教育,这种感受我一生难忘。那年周恩来总理来延安巡视,他的一言一行更加鼓舞了我们,坚定了我要为延安人民多做一些事情的决心。
1978年,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组织了四支医疗队,统一命名为北京医疗队,第四批医疗队被派往世界屋脊的屋脊——阿里地区巡回医疗一年,医疗队由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广安门中医医院、北京友谊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天津医院、新疆石河子医院共40多人组成,我有幸参与其中,并任命为大队长。
我们从北京坐火车到达新疆乌鲁木齐,再坐大巴车翻过5000米高的冰大坂到南疆,再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到喀什,然后爬上阿里高原,整整十多天才到达阿里地区。

在阿里地区与医疗队员合影
阿里地区总面积34.5万平方公里,面积相当于两个河北省,积水潭医院医疗队安排在阿里革吉县。革吉县有4万平方公里,与海南省一样大,但人口只有一万出头,称得上地广人稀,平均海拔4500米,氧气稀薄,含氧量只有北京的40%,可能会发生高原性肺水肿。
由于阿里交通不便,各县的医疗队都是独立工作。积水潭医院医疗队配备了内外科医生和妇科、眼科护士,我是烧伤科医生,但我曾在骨科、麻醉科轮转过,在广安门医院学过针拨白内障手术,所以除了为藏民进行内科疾病诊治外,还进行了多次外科和妇科的抢救手术,也给多位藏民进行了针拨白内障手术。
采访组:您是否有过国外学习的经历,能聊一聊吗?
张仲明:1985年,卫生局拟派我去小汤山康复医院当院长,我没有学过康复管理,希望让我出国进修学习。当时卫生部正好有意大利进修康复的名额,1985年秋,我前往意大利米兰的一家康复医院,后又到罗马一家康复中心进修。因为我是一名烧伤医生,也进修过整形外科,所以在意大利我着重进修学习“人体外型康复”方面的知识与经验。
在罗马康复中心整形科,有一次科主任给一名足背溃疡的病人进行植皮手术,我在台下观摩,只见他用“Humby’s”刀取皮,可是取下的皮都是破布条样的毛边皮片,这样植皮的效果会不理想。我提出可以帮助上台取皮,上台后我按照患者足背溃疡的大小,完整地取下一块中厚的皮片,稍稍进行一些修整,就严丝合缝地贴在了患者的溃疡创面上,整个过程不到十分钟。当时周边观摩的医生都很吃惊,没有想到一个中国进修医生的手术居然能做得如此漂亮。
整形科里住满了截瘫的病人,他们的臀部都有一大片褥疮,每天都要进行换药,却没有想办法去覆盖或者清除创面。在得到科主任的同意后,我用自体皮和异体皮相间移植法为病人清除了创面,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于是,康复科主任让我写了一篇关于截瘫病人褥疮创面修复的论文,并在意大利全国研讨会上发表,受到了他们的欢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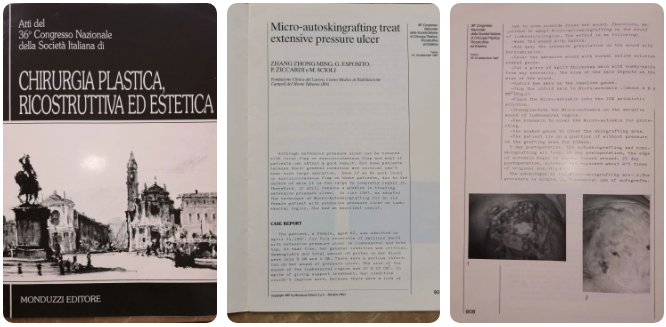
国外进修期间发表的论文
采访组:您是哪年到首都儿科研究所工作的?您刚到所里的时候,是否面临很多困难?开展了哪些具体工作?
张仲明:我是1992年来首都儿科研究所担任所长职务的,刚到所里的时候,发现附属儿童医院从环境到建筑还不如一个县医院,医院的科室也不全,医疗设备远远满足不了医疗需要,医疗质量和管理水平和同级别医院相比有较大的差距,科研工作虽名列前茅,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还远远不够。但是我们领导班子和广大职工毫不气馁,大家同心协力众志成城,艰苦奋斗,大力弘扬“慈爱、严谨、求实、创新”的首儿精神,所院工作越来越有起色,科研工作更是上了一层楼。
钱渊研究员主持的病毒学研究室,由于成果突出被市科委批准成为北京市科研重点实验室。李家宜研究员主持的柯萨奇病毒性心肌炎的课题是科研和临床相结合典范,为此,首都儿科研究所首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由于科研工作整体成绩突出,首都儿科研究所连续五年荣获市科委颁发的改革与发展一等奖。
1993年,市科委特批了首儿所科工贸一体化的中试基地和首儿药厂,实现了科研成果到医药产品的转化,也满足了儿童专用药品的生产和应用需求。同年,市科委设立了新星计划,刘哲伟同志入选,这对我所的人才培养起到了助推作用。同时,我们还选送了一批科研精英,如陈博文、吴建新、刘哲伟、冯雪莲、米杰等人到国外进修培养,加速重点培养科研人才,他们回国后都成为了我所的科研骨干,对首儿所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试基地签约(左一为张仲明)
附属儿童医院因为成立不久,医疗条件不是很好,医疗质量也有待提高。为提高声誉,1993年,我们和北京医科大学合作,使附属儿童医院成为北京医科大学儿科学系的教学医院,每年都有一定比例的儿科系毕业生分配到我所,加强了人才技术力量。此外,我所还成为北京协和医学院博士学位授权点,从此有了自己的博士生导师,可以招收博士生。
采访组:您什么时候入党的?
张仲明:我是196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时我刚刚28岁。我为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我从小就对中国共产党有着深厚的感情。小时候,国民党把我们家的粮食都抢走了,是解放军把国民党赶走了。我12岁那年,家乡洪水泛滥,我在回家的路上一脚踩空掉入河中,洪水滔天,已经淹到了我的脖子,我不停地呼喊,是路过的解放军战士把我从水里救了上来。在我心里,是解放军、是共产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后来我在医学院读书,家中经济出现了问题,我没钱继续上学了,党支部知道后就向学校反映了这个情况,学校给我申请了奖学金,这让我再次感到,党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今天。我到医院工作后,党组织对我非常关心重视,把我当作医院重点对象来培养。我把听党话、跟党走,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成终身目标。经过5年的考察,1965年,我终于成为一名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采访组:入党后,您参加过哪些党的工作,为党组织做过哪些贡献?
张仲明:我认为本职工作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应该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做好工作。所以无论我在积水潭医院烧伤科当医生,还是在北京市卫生局、首都儿科研究所做管理工作,都始终认为这是党的需要,坚决服从党组织的安排,不考虑个人得失,要像雷锋同志那样,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我调到北京市卫生局工作的时候,不少人劝我:“放弃专业太可惜了,技术丢了,职称没了,再考虑考虑”。但我不为所动,因为服从党的安排是一个共产党员最基本的要求。
在北京市卫生局工作期间,我负责医疗医政管理,还是要先抓住主要矛盾,医疗质量、医疗秩序最重要,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基于以往在积水潭医院工作的经验,我重新梳理了病程率、治愈率、病床率等各项指标,将治愈率、疗程、费用三者结合起来作为医院评审的标准,制定了医疗质量指标,规范了医疗机构的评审体系,明确了临床建设发展与能力的标准,在当时对提升医疗资源的服务效率起到了积极作用。
采访组:您是哪年退休的?退休以后还做了哪些和医院相关的工作?
张仲明:我是1996年退休的,我退休以后受中华医院管理学会的邀请,担任中华医院管理学会副秘书长。管理学会设立了多个管理委员会,专门研讨医院管理先进经验,在不断相互交流中,以提高各医院的管理质量与水平,同时也间接协助各地卫生行政部门对所属医院进行管理。我在北京市卫生局工作了十年,积累了一些管理经验,所以在退休之年,也实现了老有所为的愿望。
采访组:您作为首儿所的老所长,您认为首儿所在未来的发展中还需要向哪些方面努力?
张仲明:我是一名烧伤外科的医生,上级安派我到首儿所任所长,这是党的需要,也是党对我的信任。自叹能力有限,没有做出更多成绩。但我深知,要让首儿所加快发展,必须依靠党的组织,依靠全所科研人员和医务人员的共同努力。
近些年首儿所发展速度很快,在未来发展中要高瞻远瞩,向世界一流的研究所和医院看齐,戒骄戒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把人才引进和人才培养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发挥好现有人才的重要作用,尊重人才、尊重劳动,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平台和环境,这样才有强大的人才队伍作为支撑。
采访组:请您简短地概括一下作为医生和医院管理者的感悟,您想对年轻医生说什么?
张仲明:我的最大感悟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永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在年轻医生的成长过程中,肯定会遇到沟沟坎坎,这个时候不要气馁,多想想革命先烈,想想时代英雄,想想那些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这样就会发现自己遇到的挫折非常的渺小,这样就能找到人生前行的动力,就有了遇到挫折也能向前奔跑的勇气。